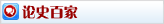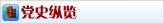永城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
发布时间:2017-6-29 11:32:31 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23042
永城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
------忆永城学生大队
魏启民
灾难深重的豫东永城人民,为求翻身解放,历史上曾多次参加农民起义,但都一次次地失败,遭到统治者的屠杀;在各个历史朝代,也都有大批农民,不甘于贫困,外出吃粮当兵,结果也是暴尸他乡,当了统治者的炮灰;还有一些日在饥寒交迫中,铤而走险沦为强盗。然而,在这块所谓兵多匪多的土地上,从未出现过一支人民组织的人民武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及其以后的“立三路线”时期,永城人民的优秀儿女,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们,试图通过暴动夺取政权,成立人民武装,但也失败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漫长而艰难地等待、摸索,组建永城人民武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938年5月,日军占领永城。几十万中央军由徐州经永城溃逃而去,土匪杂八队蜂拥而起,永城人民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迫切需要一支人民的武装,抵抗日寇的侵略。在广大青年学生投笔无路,请缨无门之际,为顺应永城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的抗日需要,中共永东支队在1938年夏秋,便着手组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永东抗日学生队。
学生队,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但星火很快燎原,到1939年4月,便发展到具有全县规模的四、五百人的学生大队。1939年6月,又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四师的前身)独立大队。他高举抗日红旗,朝气蓬勃地战斗在豫皖苏边区。
如果说,永城沦陷前,永城县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领导的抗日救亡学生队,是一支具有高度抗日热情,从事抗日宣传和清除弊政等进步活动的抗日救亡团体,那么后来重新组建的学生队,则是曾受到动委会学生队的影响,启迪,在我党我军(先是八路军,后是新四军)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它虽还沿用“学生队”的名称,但在质的方面已经升华,由抗日救亡学生队,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军。
因而,党组建的学生队,实际上是一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军。它集中了几百名优秀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是原动委会学生队的成员),投笔从戎,并带动了大批青年农民参军。他们纯洁热情,忠诚无私,富有强烈的民族感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一旦拿起武器,穿上军装,便成了英勇无畏的战士。
现就几个方面,对学生队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组建
日军进永,激起永城人民的极大愤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中央军溃退丢下大批武器装备,永城出现了组建人民军队的大好时机。但这时由于永城党的力量较小,又无思想准备和组建军队的经验,结果大批武器落入土匪、流氓和地主豪绅之手,形成了无数股杂八队和三里一队长,五里一司令的混乱局面。个别共产党员掌握了小队枪支,日军来后也没能利用。如中共永东支部党员李品立任吕店的联保主任时,领有三十人枪的“谷仓队”,鬼子来后,解散了。吕店“谷仓队”的枪,除李品立留下一支卜壳枪,蔡玉琨(蔡新铭的父亲)扛走一支套简,给冀铭武一支十子连,另几只藏在练刘庄刘桂芝家外,其余都摘下枪栓丢在练刘庄后孙庄前面的苇坑里(蔡新铭说丢在何营子井里,反正是掩藏了)。杂八队起来后,怕被搞去也未敢捞起。
杂八队起来后,散处在永东北丁、陈集子和刘河一带的原动委会学生队的刘传新、刘宝亮等,主动找到盛瑞堂,要求组织青年武装,宣传群众并争取杂八队抗日。盛同意后,便向陈仪如要了15支枪,于1938年旧历五月底在杂八队司令陈体俊司令部附近的梁油坊,集合了十五、六个青年学生和个别青年农民,成立了一支以武装宣传抗日为主要任务的学生队。不久,扩大到三十余人,分为三个小队,刘传新、刘宝亮、盛老四(盛瑞堂的堂弟)分任小队长。队员有:刘须彦,王兆明,梁永泉,窦广堂,吴士昌,周尚文和王楼的俩个青年学生,....等。活动于丁、陈集子和王集一带,但组织较松散。秋天,很多人生了疥疮,较重的便自动回家治疗,到年底只剩下十余人。
这支学生队中有两位党员:吴士昌和盛老四。他们是在建队前盛瑞堂发展入党的。在队里,盛瑞堂经常向队员进行实事、政治教育,讲八路军和萧县抗日的情况,通过李品立学生队的成立和发展,有时还进行党的知识教育。
这支小小的队伍,隐蔽地活动于浩瀚的杂八队的夹缝中。在当时虽没能产生较大影响,但它是永东北学生队的先导,为后来的发展准备了骨干,打下了基础。
1938年夏,盛瑞堂、李品立和屠庆太曾试图争取冀铭武,想把冀的部队置于我党的影响或控制之下,成为一支抗日力量。
冀铭武有支五六十人学生队。当时考虑:他是个青年学生,对李品立、屠庆太有师生亲朋关系,有争取的可能性;他父亲冀思涵与王胡子是朋友,他易于存在。
具体的做法是:以盛瑞堂的名义,由李品立、屠庆太出面,召开高庄一带的青年抗日座谈会,邀请冀铭武参加。在会上宣传抗日救亡,会后有屠庆太出面和冀铭武结拜为交;然后,与冀研究成立抗日团体。经冀同意,在李楼李品立家的最后一次会上,宣布成立“永东青年救国团”,冀绍武为团长,屠庆太为参谋,陈品超任军需。盛瑞堂的十几支枪,也归屠“青救团”。由于冀绍武和?队匪性难改,和共产党格格不入,争取工作失败。
同时,盛瑞堂还指派屠庆太打入杂八队八队王老三部,以王老三的秘书
的名义出现,掌握杂八队的动向,并乘机从中组织自己的力量。后因王老三对毫无实力的学生不放在眼内,使屠庆太在王部无所施展,不久就离开了。
1938年深秋,永城农村已十室九空,呈现一片凄凉景象。人们心灵中,蕴藏着被践踏、奴役的悲伤,广大爱国青年,胸中燃烧着抗日复仇的怒火:永城农村已布满了抗日的“干柴”,组织人民武装的政治条件,十分成熟了。
这时,杂八队的势头在永东也大为减弱。王胡子准备外走,走前去永西进行最后一次抢劫,绝大部分离开永东老窝。之后不久,王老三部去陇海路北投奔国民党五十七军于字忠部;王胡子被委派为中央军的“师长”,也跟着国民党天水行营程潜部派的一个湖南人叫汤秉南的特派员去许昌。苗桥、茴村一带的王洪范部杂八队,旧历九、十月去兴化泰州投奔李明扬。当地只剩下些小铺杂八队,大大减轻了我党活动的外部压力。
在此形势下,中共永东支部决定利用大好时机,着手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分工李品立、屠庆太在高庄一带成立一支队伍;盛瑞堂在永东北做争取红枪会的工作。
分工后,盛瑞堂派屠庆太去萧中县委回报,之后盛瑞堂又亲带李品立去萧中县委,并由县委组织部长带盛、李二人去陇海路北找八路军请求指示和帮助。盛、李去萧县时,带去三发国民党丢掉的大炮弹,作为对八路军的礼品。三人一人抗了一发炮弹到陇海路北属于砀山县的一个村庄,找到了八路军领导机关。从八路军回来后,便开始了永东学生队的组建工作。
事先,李品立曾向准备入队的部分人员分送了一些八路军的宣传品。如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国民党消极抵抗黑暗腐败,《近?魔的下台》等分析国共两党和中日双方形势的材料,使大家思想上对国共两党和抗
日形势下有点初步认识。同时,发展屠庆元入党,为建队准备骨干力量。
然后,李品立、屠庆太(主要是李品立)分头通知参加学生队的人于某月某日去某地集合,到八路军去受训。被通知的人,均是品立、庆太的同学、学生或亲朋好友,都是具有初中或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
魏庄和我同去“受训”的有比我小两岁的谢金洲(现名谢光武),两人都是李品立的学生。1938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穿了一身夹衣,一件旧兰布大褂,背着中央军丢下的一条旧质军毯,分文未带(家中连一角钱也拿不出),乘着带有凉意的秋风离开了家庭。
集合地是高庄东南十五华里、汴河南岸、永城二区五湖乡的周圩子村(解放后划归安徽濉溪县)。周圩子是豫、皖交界之处,偏僻、隐蔽,气氛宁静,周围无杂八队居住,是个十分理想的从事政治活动的地方。
集合后才知道不是受训,而是成立永东抗日学生队。由于心情十分高兴,也就不管受训不受训了。至于为什么叫学生队不叫别的名称,李品立的解释是:我们的部队是以学生为主体,叫学生队比较符合实际;学生队,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对青年学生,学生队便于和杂八队区别。当时,这个队那个队很杂乱,王胡子叫“东进支队”,北边王楼的一个司令叫“挺进支队”....,我叫学生队,可一新人的耳目。
第一天去集合的约20人左右。除李品立、屠庆太外,还有:(屠庄的)屠庆元、屠庆春、屠运乾;(蔡楼的)蔡振钢、蔡湘(后随王胡子西去);(张石桥的)张宗顺、张训让;(葛店一带的)张化东、邵士杰、陈品超;(高庄一带的)赵子杰、魏启民、谢金洲等。当天去的还有萧县县委派去的秘密交通员赵金财和从萧县来的赵健民。
赵健民,我党早期党员,后脱党。他由萧中县委介绍到盛瑞堂处。在学生队负责宣传教育,没有职务。1939年春节后离去。
集合的人中,除外来的“两赵”懂些革命、抗日道理属于“洋八路”外,其余都是当地的“土八路”。土、洋汇合后,“洋八路”想很快传授其“洋”,而“土八路”则急于摆脱“其土”。所以集合的当天,大家便兴高采烈地围着两赵,十分新鲜地听他们讲八路、共产党(当时还不知道新四军)。他们从苏豫支队讲到萧县的十七大队(朱茂修部)、十八大队,....。当天还教会了两首歌:《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晚上躺在地铺上又听他们讲了很久才入睡。一边是口若悬河,想把知道的东西一下子向大家倾泻出来;一边似大旱望雨,想把听到的新鲜事儿尽收入“干枯”的胸膛。一群众年青的“土八路”们,从此思想似?然升华,豁然开朗。大有当八路一天胜读十年书之感!
第二天离周圩子去高庄一带活动。差不多每天都有新队员入伍。到1938年底,已扩大到四、五十人,编成了六个班。这段时间来的有:蔡新铭、张彦秀、蔡新简、葛昌文、张传新、郭××(葛店附近郭庄一青年农民).....等。
永东学生队只李品立有支卜壳枪,其余都是徒手。即是部队怎能没枪?可是当地枪支,全被杂八队收走,自己又无能力从敌人手中夺取,从哪儿去搞哪?天无绝人之路,在似无办法中终于找到了办法:
偷枪。王胡子杂八队,当时很多人不干回家,出现了枪多人少的现象。杂八队管理松散,头目们对枪支无数。李品立便利用关系从王胡子杂八队中偷出十几支枪。
找枪。李品立把原“谷仓队”留下的枪又找回来几支(多数无法再用)。
夺枪。1939年春节前,王胡子队伍西去时,一些人在永西携械逃回,他们把枪装在口袋内用小土车推回永东。学生队住屠庄一带时,陆续查获了十多支。有一次就查获七支,是黄昌忠部下大队长黄思伦的枪(黄思伦本人也逃回来),由于黄思伦是屠庆春的内兄,又把这七支枪还给了他们。
主力支援。1939年春节后,张震参谋长率部在高庄消灭了王胡子的残部后,赠给学生的25支枪,为永东北、永东两个学生队分用。
1939年春节后,永东学生队已拥有四、五十支步枪,基本做到人手一枪。记得1938年年底第一次发给我一支德国造套筒枪时,十分高兴,很快学会了装卸、擦拭,并在屠庄西头朝天放了一枪以表庆祝。虽然扛起枪来还有些不太协调,但却硬要表现出兵的样子来,颇令人好笑。
1939年年初,永东北杂八队也趋衰落。陈体俊被日军打死,部队解体;董四方受日军打击后,人也不多了。永东北学生队变活跃起来,部队迅速扩大。这时,去永西寿松涛处学习的刘传新也回到部队。到39年春节后,永东北学生队已发展到六七十人,新四军游击支队派乔厂(han)、徐干(童振铎)、李士昌来任政指、队长和分队政治战士,骨干力量大为加强。刘传新这时以永东北学生队指导员的名义,作为盛瑞堂的助手,来往于永东两个学生队之间,兼给永东学生队教歌和做些宣传工作。1939年3月,永东两个学生队就常在一起了。
1938年冬,寿松涛受彭雪枫的派遣,率13位从延安学习回来的浙江同志,到驻在永西龙岗集的河南商丘专区保安第三总队蔡洪?部政治部作统战工作(蔡兼任顽永城县长),和徐风笑带去蔡部的十几位宿县的同志汇合,在龙岗西面的管沟村,办了三期干训班,毕业后一部分分配在蔡部任营连的教导员和指导员,一部分回家乡做抗日宣传工作。永西、永西北(少量宿县和永东)的大批知识青年,去寿办干训班受训,受训回家的一部分永西知识青年,根据党的指示,于1939年春节后,又在酂阳集重新集合,由蒋汉卿率领去书案店新四军游击支队支队部受训。受训后,宣布成立永西学生大队。
去书案店受训的学生约三十余人,多数在寿办干训班受过训,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原酂阳完小的学生(有的已是初中学生)。他们是:蒋汉卿、刘晓华、刘晓宇、刘晓东、丁名道、丁汝勤、丁汝琛、谢俊杰、谢俊卿、张启先、王文味、王文俊....等。
第一天之后走到书案店,蒋汉卿作为代表先行前往。他找到游击政治部肖望东主任。第二天大家到达书案店后,在支队随营学校速成班(有的说是教导队)受训两周。授课教员是:周秀方(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讲政治;钟友松(支部司令部参谋),讲游击战术;程致远(支部司令部科长),讲军事动作和负责制式教练;肖主任有时也讲讲形势。受训后发枪20支(内有一小全钩为谢俊卿使用),宣布成立永西学生大队。任游击支队参谋(或教导队排长)杨斐为学生大队大队长。
永西学生大队成立后,即回酂阳一带活动。活动范围在酂阳、十八里以北,即老永商公路以北,县北陈集子以西,蒋口一带地区。
不久,支部派王振亚任永西学生大队的中队指导员(大队下属一个中队),部队也随之逐渐扩大。刘永岑、尹传良、赵秀等也来学生大队。这一时期参加的还有:丁汝海、张朴、刘来泰....唐庸之也常随永西学生队行动。蒋汉卿、刘晓华等同志,因要去永城一区工作,故在学生队未安排职务。
王振亚在永西学生队任职不久,乔厂接任政指。游击支队司令部参谋郭仲涛,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副大队长兼中队长。郭仲涛走后,支队派陈体恕任永西学生队中队长(陈可能从支队随营学校来)。
这时的永西学生队,有五个班,约五、六十人。
二、锋芒初试
学生队成立之后,大家较缺乏部队工作知识,仅凭一股革命热情,试着做了几项应当而且能够做的事。
进行抗日宣传,唤起民众抗日,这是做得较多、较普遍的一项工作。
首先,是大唱革命歌曲。唱歌,既是向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又是对学生队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课程;同时,也是与杂八队区别的重要标志。很多歌曲唱起来令人激愤,催人泪下,甚至现在哼起来还叫人难以平静。唱歌,还启迪、陶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跃部队生活。因而学生队成立之后,便把学歌、唱歌当成一件大事,一种学习,几乎无日无时不唱。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4月,永东学生队大约学会了四十余首抗日歌曲,有时还旧曲新词自编自唱。学生队学会了就唱给群众听,每每唱着歌儿进村,唱着歌儿出庄。正如一首歌词中说的“汗淌淌,乐洋洋,唱着歌儿进村庄”。随之,嘹亮的抗日歌声,响彻永城大地。
为供了解,现抄下曾唱过的两首歌的歌词: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走啊……!
一身血和肉,付与民族有,誓去雪我国耻复我仇。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走啊……!
鬼子侵华夏,野心夺神州,种种惨剧积聚在心头!
同胞们,齐奋起,敌人扼咽喉,怎么不还手?
同胞们,齐奋起,抗战仗自己,莫再仰欧美!
走啊,向前,向前,向前走,走啊……!
我们不奋起,中国由谁救?早晚一死莫在亡国后!
《我不愿做奴隶》
我不愿做敌人的奴隶,我不愿受人的欺凌,我宁肯离家去当兵,去打倒横暴的敌人!
日本强盗狼子野心,他夺去了我们的东四省,又抢占了平津和我们的上海南京。
我们要报仇雪恨,把强盗赶出国境,去复兴我中华民族,死也要拼命打倒敌人!
抗日宣传的第二个方法是进行街头演出。每到一寸,都演出有抗日内容的双簧、快板、戏剧等节目。李品立、刘传新在这方面尤为活跃。刘传新经常和吴士昌一起演双簧,唱“月亮一出照楼梢,听我唱个抗日小调……”。刘在后面唱,吴在前面演,最后以反复几个“哎呦”而结束。生动活泼,颇有风趣。李品立自编自演的快板《说洋》,寓意鲜明,也很受欢迎。大意是:
说东洋,道东洋,东洋小鬼太猖狂。
洋人、洋枪、骑洋马,挎着洋刀气洋洋。
说洋话、调洋腔,“八格亚路”洋屁放。
东洋胡,东洋装,一脸横肉没人样。
自从洋人来永地,黎民百姓遭了殃,
杀我同胞无其数,奸淫多少大姑娘!
亡国奴,太凄凉,牛马生活苦难当。
于其活着受洋罪,不如拼死干一场。
拿起刀,扛起枪,人人奋起杀东洋。
夺他洋枪和洋马,为民除害乐洋洋,
乐洋洋!
描写日本人践踏中国土地、欺压中国人民,最后激起反抗,把日本兵打倒的《哑剧》,是永东学生队的拿手好戏。此剧,赵建民导演,日本兵常由赵建民、李品立或张宗顺扮演,张训让,张彦秀,屠庆春、魏启民、蔡新洁、张化东、蒯汉杰等,则扮演群众角色。日本兵调戏侮辱妇女,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人一齐奋起,打倒日本兵。然后,齐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作了结束。演出中间,群情激奋,老大娘流出了同情之泪,当中国人围攻日本兵时,会场上爆发热烈的掌声。
学生队还用实际行动扩大影响,从事无声的宣传。上门板,捆铺草,不拿群众的东西,尊老爱幼,老大娘长,老大爷短地叫个不停。群众看到这样的部队不仅有新鲜感,而且又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举两例:
1939年春节前的一天,永东学生队去茴村南的韩楼,刚进西门,看到东门来了一铺杂八队。群众认为都是杂八队颇为惊慌,李品立当即命令学生队原地休息,唱歌,群众情绪才稍稍缓和。后经李品立和杂八队商定,一边马走东头,一边马走西头。学生队住下后马上化妆演出,而杂八队却忙于派饭捉鸡。韩楼的群众和杂八队员被我们的演出吸引过来,杂八队头头十分尴尬,饭后灰溜溜地离韩楼而去。
又一次,永东学生队去高庄北的谢店村。离村半里,庄上的群众有人外逃。李品立叫部队停止,还用老办法:唱歌,让张训让吹号(张兼司号号),歌声和号声,使群众认出是学生队(杂八队是从来不唱歌不吹号的)。李品立进村,找到村中开明士绅吴子丹,说明来意,群众方化忧为喜。
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也活跃了部队,融洽了上下关系。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演戏,说说笑笑,热闹非常,虽有领导和被领导之分,但从外表很难分出官兵来,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
生活上,大家一样艰苦。不发零用钱和任何实物,衣、被、牙刷还要自备。但大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有时,实在馋的无法,则下塘摸泥鳅(不敢捉群众的鱼)改善生活,大家一起摸,一起吃。
称呼上,还不习惯称同志,除盛瑞堂年大些,大家尊敬的叫他老盛外,其余均直呼其名:品立、庆太、传新、宝亮、法言……。这样,大家颇感亲切,许多同志一直把这种称呼保持至今。
互相间,相亲相爱,无拘无束。没有人摆架子,也没有人板面孔。李品立平时幽默,风趣,有讲不完的故事和笑话,因而大家很爱接近他,有时,一群小青年把盛瑞堂围上,请他讲这讲那。他除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外,也讲点当地的神话。有次夜行军,老盛就讲了丁集子的“老猫猴”和苗桥会上炸花炮的事,使大家之间困意全消。原来。老盛也是讲故事的能手!
有些小同志,行军时爱瞌睡,大同志就拉着他们走。有的人很脆弱,爱哭。一有人哭,老大哥们就哄将起来,直到逗笑为止。
学生队胜过家庭的温暖,大家对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愿离开它。有这样一件事:
1939年春节前夕,一个队员家中要他结婚,说:兵荒马乱,姑娘在娘家怕担风险,日期已定,要提前回家。“在学生队怎好结婚?”可是又不敢抗命,这个队员就一面应付家庭:“到时再说吧”;一面向上级表示:“坚决不结婚,请把部队拉远点,叫家里找不到。”可是,活动的范围就那么大,怎能摆脱群众的追踪,所以那几天,不管走到哪,家中总是有人来催。当天上午,家中去催的人更是心急火烦了,领导也只好劝其回家:“已经准备,不回去不好,况又是品立母亲的媒人,不然老人家也下不来台。”在无法再推的情况下,只好回家。花轿已快来临,借了几件衣服,剃了头,草草地拜堂。次晨,仍不顾家庭的反对又匆匆的离家归队。父亲在后面边追边喊:“不过三天,不兴空房的,快回来……!”“知道了,晚上就回来……”,老人追不上,懊丧地回家了。
类似的例子,在学生队似不止此一人。
学生队的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影响日益扩大,部队随之迅速发展。1939年年初,有大批学生和青年农民参加永东两个学生队,能记得名字的有:翟宝三、翟宝树、蒯德修、蒯德润、刘须钦、刘须兰、党阳合、周法言、蔡铎、陈品廉、蒋相半(寿松涛的警卫员)、张宗仕、蒯汉杰、蔡新安、蔡振铎……
值得一提的是周法言同志的参军。
周法言同志家中只有他一个有文化的人,家庭不愿他出来。当他知道学生队真正抗日又很文明时,便说服家庭坚决来到学生队。当天,他穿了一身新,像走亲戚、办喜事一样,非常高兴。初来时,他不会唱歌,一唱别人就笑,一说话脸就红,纯朴、热诚,十分可爱。入伍后,由于他学习认真,工作踏实,不怕别人笑话,他不仅很快学会了唱歌,而且各方面都有飞快进步。不久,他就成了学生队的骨干。在艰苦的斗争年代,他又很快成了我军的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坚强的政工干部。
学生队建队之初,注意了建党建军工作。
永东北学生队,建队后,除及时发展党员,进行党的教育外,三八年底还派本队骨干刘传新、刘宝亮去永西寿办干训班学习(刘宝亮因痔疮较重未去成),刘传新在干训班入党。1939年年初,乔厂任指导员时,又在队里发展了刘宝亮等一批党员,成立了党支部。
永东学生队,三八年底派屠庆元去苏鲁豫支队受训两月,回队后任指导员。1939年一月,李品立又在屠庄发展了屠庆春、蔡振纲、张化东、张彦秀、魏启民等入党,建立了永东学生队党支部。
永西学生队,王振亚任指导员,发展了谢俊卿等一批党员,也建立了党支部。
这样,1939年初,三支学生队都建立了党支部。
1939年初,永东北、永东学生队,都建立了队,分队和班,配备了军政干部。永东北学生队队长徐干,政指乔厂、刘传新;分队长陈继增,盛老四和xxx;政治战士李士昌,刘保亮,翟宝树;队部文书刘须彦。永东学生队队长陈品廉,政指屠庆元;分队长屠庆春,党阳合,张宗化;分队政治战士邰士杰,张训让,张宗顺;队部文书兼医生蒯汉杰。永东学生队班里也没有政治战士,我曾任过班的政治战士。
建立行政组织的同时,也开始了军事操练,但不严格。
学生队还经常注意与外部的联系与配合。三八年年底之前,永东学生队除赵全财外,还派屠庆春去肖、宿和陇海路北八路军联系。屠庆春能吃苦,泼辣可靠,而且脚大腿长,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被誉为“汽车腿”。
永东学生队有时和宿西李时庄部队靠拢或配合行动。李时庄部的宣传队长汪木兰,是位胖大的姑娘。她曾和我们讲过话,我们也看过她们的对外宣传。见过汪木兰后,李品立便经常讲她的笑话:一次日本人扫荡,汪木兰走不动被担架抬着,四个抬担架的人压得嗤牙咧嘴,抬不动。又让她骑毛驴,结果,毛驴也压死了。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为此又产生一条歇后语:“汪木兰跳井——下不去”。
除上述工作外,学生队还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打击汉奸土匪,在和日、伪、顽匪的斗争中生存发展。这里择要读几点:
(一)监视王胡子杂八队的行动。
王胡子走前,学生队常派人去王胡子司令部,通过王胡子的军法处长杨福顺了解王内部情况。因此,永东学生队对王胡子部队了如指掌。由于我军尚难消灭这样的大股力量,也只能对他监视。
1939年1月,游击支队派腾海清来永东了解匪情。腾通过盛瑞堂找到李品立。在李品立家,腾和李品立、屠庆太研究了去见王胡子的事,以和王联络为名,探听王的态度和虚实,以便进一步确定我对王的态度。李品立叫屠庆太、陈品超和屠庆太的大爷(庆春的父亲)屠振彪带腾去见王胡子。王对腾虽以礼相待,但他看不起新四军,同时国民党的收编大员已到达王部,,故王胡子闭口不谈与新四军联络的事。腾此行虽未达到“联络”的目的,但却亲眼看到王胡子和王胡子部队的情况。
(二)配合主力消灭王胡子残部。
王胡子走时,王老四部,于西奇的“宪兵营”,“两黄”(大小秋叶子:黄永清、黄昌忠)和他们的一部分部队未跟走。1939年春节期间,杂八队驻在高庄和其周围的谢阁子、蒋高台子、蒋香庄一带过年。游击支队了解后,张震参谋长率腾海清大队迅速插入永东。张参谋长找到盛瑞堂,请永东的党组织向他们提供情况,然后制定行动方案。张参谋长经与盛瑞堂、李品立等研究后,由永东学生队带路,先搞掉了茴村李永复组织的伪政权,永城二区良民区,然后,李品立、陈品超回高庄,摸清高庄一带杂八队的情况,画好地图,由李品立的二哥李品方(他在西北军当过兵)带着地图,把新四军领来高庄,李品立、陈品超则在家掌握杂八队的动态。1939年春节后的年初四(或初五)拂晓,新四军从茴村到达高庄,杂八队毫无提防。我军按事先部署,在李品立、陈品超的带领下(部队到高庄时,李、陈也赶到),迅速解决了高庄、蒋高台子、蒋香庄号称三个营兵力约六七百人的杂八队。谢阁子、王老四部,因与李品立已有联系,我开始了对王老四的争取工作,故来劝他。“两黄”、于西奇等头目,均在家过年,杂八队群龙无首,加上没有提防,部队松散,故我仅用一个大队兵力,无一伤亡,很轻易地消灭了敌人。除在高庄刘长清饭馆击毙几名企图顽抗者外,杂八队的大部人员均弃枪逃跑,捉了少数俘虏,其余我未进行追捕(我无法收容许多俘虏,且杂八队大部是农民,开枪射击并不合适,任其逃走了)。
这一仗,胜利大,缴获多(都是好枪),新四军声威大震。从此,王胡子部队只剩下了人数不多,对我无甚威胁的王老四部了。这一仗,为永城二区的开辟起了关键作用。
(三)争取王老四归顺。
王老四叫王景玉,是王胡子的四弟。以前当长工,只是在王胡子拉起部队后,跟着拉起一小铺部队。他本质与王胡子、王老三不同,未有很大劣迹,具有为我军争取的可能性。
王胡子、王老三走后,王老四六神无主,又害怕新四军,于是便主动向学生队、李品立靠拢,常撇开他的一帮参谋,单独向李品立请教。新四军打高庄前,李品立事先告诉他不要乱动,新四军到高庄西头时,王老四很怕,又派人向李品立请示,李品立告诉他别怕,没他的事。王老四听了李品立的话果然没事,以后他便相信和靠拢李品立。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争取王老四的良好时机。
经盛瑞堂同意,1939年旧历二月初,李品立派永东学生队的屠运乾、张化东二人去王老四部,开始了对王老四部队的进一步争取工作。
屠运乾的本家哥屠运德是王老四的中队长(王部只此一个中队,一百余人。原叫大队,王胡子走后,改为中队),屠运乾以中队事务长的名义,作屠运德的助手共同掌握部队,张化东任政训员(类似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和教歌。我们要求王老四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王一一答应。屠、张二同志除向王部进行抗日、爱民教育外,还与屠运德一起,通过结拜的方法,团结王部的下一层官兵。以后王老四虽有反复,但他的六七十人的基本队伍,1939年秋终被屠、屠、张三人带到李品立任区长的永城二区编入区队。
1939年秋,当王老四只剩下贴身的十几个人时,屠仍托徐风笑在高庄开药店的亲戚陈永宫带领,向我永城县政府(在永南杨园)投诚。由于我当时采取对王老四急于消灭的政策,王投诚不久,他的一伙(包括他老婆)都被杀掉。《永光报》头版头条报导了《大土匪头子王老四伏法》的消息。因二区李品立等对杀王老四有不同看法,报上又刊登了《谁说王老四不该杀》的反驳文章。这一杀,给后来对其他部队的争取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被动,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
(四)和地方顽固势力斗争。
1939年年初,永东学生队已初具规模,永城二区区长冠运生①仍打起学生队的主意,想把学生队编入他的部队。他不便直说,便请鲁雨亭出面给李品立谈。1939年春的一天,鲁雨亭在李品立家,转述了冠的意思。李品立说“把学生队拉走也好”鲁看李不高兴,即告别而去。(据说,鲁此行是得到寿松涛同意的。)
事后,李向盛瑞堂谈了此事。李说:“冠运生是什么东西,解放前他当区长和文教区员王瀚云一起克扣小学教员工资,我告了他多年没把他告倒①,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怎能再叫他骑在我们头上?他莫做梦,我宁愿解散,也不能把学生队交给他。”盛、李一致表示,不是上级党委正式决定,谁也别想把学生队拉走。
冠运生以后还不死心。有段时间他对永东学生队“热乎”起来,和学生队主动靠拢,以区长身份向学生队讲话,把学生队夸奖了一番,发给每人两角钱的二区“流通券”(冠分的票子),送给两筐大头菜。因李品立已胸有成竹,故尽量让她表演。最后确感无望,冠才作罢。
(五)打击汉奸土匪。
为打击日寇在乡村的爪牙,永东北学生队1939年二月,在陈楼的谢阁学校旁,枪毙了曾为日军带路、送情报的汉奸窦广窜。
窦广窜是个鸦片烟鬼,日军来后,当了日军的便衣侦探,被我俘虏。当时学生队中还有人没打过枪,更没杀个人。杀窦广窜是首开杀戒。
不久,永东北学生队又在陈楼缴了杂八队旅长丁搴子部的械。
丁搴子原是土匪,日军来后,他拉起杂八队。国民党从徐州撤退时,68军军长刘汝明住萧县李石林,永城二区区长王洪范前往晋见,王被刘封为“永宿民军司令”。王就打着这一旗号到处加委扩充实力。他委王胡子为民军第一支队司令(王胡子未听他指挥),委丁搴子为民军第二支队司令。加委后王胡子(王景昌)改名王振亚,丁搴子(丁相朝)改名丁耀东,各起了一个雅号。丁搴子的“旅长”大概由此而来。
1939年年初,丁搴子已势单力孤,又摄于新四军声威,经我争取,他便把他的三十多名基本队伍,编入永东北学生队。编后,他对我仍存戒心,想待机而变。为免生意外,我便当机立断将其缴械。缴械的场面颇有趣:由队长徐干带队出早操,变换队形时,使双方的人插花并列,然后坐下由徐干指挥唱(枪口对外),徐领唱第一句后喊:“一、二,”我方人员一齐动手抓丁部的枪进行的很顺利。余下村头丁搴子的两个岗哨,由盛瑞堂、刘宝亮完成了缴械的任务。丁部的人有十几个参加了学生队,其余解散回家。当天,丁搴子本人不在。
与此同时,永西学生队也捉了两名汉奸,一个被我枪毙,一个罚款四百元警告释放。
三、合编后的永城学生大队
为统一领导,加强工作,上级决定永东、永西的三个学生队,编为永城学生大队。大队是在永城县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独立武装力量。
成立大会:
1939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四支队伍,映着明媚的春光,伴以嘹亮的歌声,从四个方向汇集到永东盛营子附近的岳庙村南的柏树林里,排成讲话队形席地而坐:永东北学生队与刘子章学生队背北面南,永东学生队背东面西,永西学生队背西面东,情绪十分活跃。真是:三山聚义,共建学生大队;四方汇合,同唱抗日战歌。
杨斐担任会场指挥兼司仪。互相拉歌后,接着领导和来宾讲话。
首先,盛瑞堂代表上级党,宣布永城学生大队成立;宣布了干部名单和各中队序列:
大队长 王振邦(红军干部,游击支队派来),
政治委员 盛瑞堂
副大队长 杨斐
总支书记 李品立
永东北学生队,为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徐干,指导员刘传新。
永东学生队为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陈品廉,指导员屠庆元。
永西学生队为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陈体恕,指导员乔厂。
刘子章学生队,为大队第四中队。中队长刘子章。
学生大队设宣传队。宣传队队长刘传新(兼)。
大队指导员 王振亚。
大队部书记 蒯汉杰。
宣布后,盛瑞堂作了简短讲话。然后,王振邦、李品立和王卓然(来宾)相继讲了话。
李品立讲话前,先来了一段类似单口相声的开场白:
说的是,
无木也是乔,有木也是桥;去木添女变了娇。
娇,娇,娇;爱,爱,爱;难吃上烙馍卷着豆芽菜!
无足也是奚,有足也是蹊;去足添鸟变为鸡。
鸡,鸡,鸡;蛋,蛋,蛋;都被杂八队吃了派饭!
无水也是仓,有水也是沧;去水添金变为枪。
用我们的枪,枪,枪;刀,刀,刀;去对付鬼子的洋枪和洋炮!
李品立的讲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领导讲话后,刘传新宣布宣传队队员名单。人员大部分从一、二中队挑选,我和张训让、蔡新洁等都入选。刘子章中队的两位妇女张士俊(张大厂人)、吴淑坤(城内来的女学生)也入选。宣传队集合后,整个成立仪式结束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徐干指挥一中队缴了四中队的械。四中队的三十多人,除两名妇女外,一律解散回家。大家估计,这部分一定不是好人,否则,不会缴他们的械。
1984年4月,我曾为此请问李品立。李说:刘子章自以为是大革命时的老党员,目中无人,背后说“盛瑞堂算老几?”盛听了说:“永城只有一个党员,没有两个党员。”成立学生大队前,盛与刘传新的意见,缴刘子章的械,李品立同意。在成立学生大队时实施了这一计划。
刘子章部队,也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男队员中有徐显庚、丁祖凡等。
第一次“长途行军”
学生大队成立后,便进行长途行军。从永东经永北到永西北,浩浩荡荡行程百里。行军中大家精神抖擞,笑逐颜开。行军途中休息时和部队进村后,都特别活跃,除互相拉歌外,还由各中队和大队宣传队表演节目。最受欢迎的是吴淑坤表演的歌舞《蝶恋花》和《寒衣曲》;刘传新、刘永岑等人表演的双簧;陈继增跳的踢踏舞等节目。有时也欢迎大队干部杨斐、李品立等来个节目。即使不很活跃的徐干、陈体恕、刘宝亮等,也活跃了起来,带头拉歌和指挥唱歌。因而,学生大队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把部队围在中间,像逢集赶会一样热闹。
一百里路的行军,对一个老战士来说,算不了什么,然而对于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对于未离开过家门的人,却是一件大事。在他们看来,一百多里就算很远了,何况还要跨越封锁线,冒着日军出击的危险。学生大队一没经济来源,二没较好的装备,又值青黄不接,生活十分艰苦。在这种时候离
家远行,即或未离县界,也无异于一次小的“长征”。但由于热情高,思想工作活跃,官兵同甘共苦(大队干部还没有马),故行军十分顺利,未出现逃亡,成了学生大队成立之后的一次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学生大队经受了第一次考验。
第一个战斗行动
学生大队到达蒋口一带时,第一个战斗行动就是捕捉刘子源。
刘子源,永城一区刘岗人,是国民党一区区长,地方劣绅。他暗中勾结日伪,不除掉他,一区的抗日局面无法打开。
刘子源是学生队队员刘晓华、刘晓宇、刘晓东的伯父(刘晓华、刘晓宇这时在一区作地方工作)。刘家三兄弟大义灭亲,他们提供线索并由刘晓华亲自带路执行这一任务。担任捉刘的部队是一中队。刘捉到后,看押在一中队,准备以后处理。
同时,还在蒋口一带捉到一操山东口音的秃子,据说是敌探,审讯后处决了。
宣传队的风波
在永西活动一段时间后,学生大队回师东向,又回到高庄、大茴村、吕店子一带。这时的学生大队,除歌声外,又有了操练声。歌声伴着整齐的步伐,显得更有生气了。
这时宣传队出现了小小的风波。和吴淑坤一起来的张士俊,对学生大队毫无感情,一人常做祷告(她是耶稣教徒,她哥哥是张纯智是个反共派),在吕店子附近时,她提出不干回家的要求,并邀吴淑坤同行。刘传新未加慎思就同意了。她们走约半小时刘传新恍然大悟,感到不应放吴淑坤走。于是带着张训让等跑了五、六里路,又把吴淑坤追回。大白天演了出“追吴”的喜剧。其实,吴并非想走,只是碍于情面不好拒绝张的要求,同时,误认为领导真的想叫她走。幸好有这“一追”,不然,一个革命同志,便被“放”走了。
宣传队成立之后,刘传新热情很高,除教歌排节目外,还经常找人谈话,其中和吴淑坤的接触便多起来,于是引出了闲言。大队领导为照顾影响,把刘传新调回一中队,李品立兼任宣传队长。不几日,陈杰(徐干的妻子)从随营学校调来任宣传队长。
陈杰,年青漂亮,参军前是蚌埠城内的中学生。日军来后,逃难到乡下徐家与徐结婚。可是陈到宣传队不久,就与徐疏远,为个人问题无心于工作,加上缺乏能力,故她去后,一些宣传队员纷纷离去,宣传队濒临解体。
剿匪除霸、打击顽伪
三中队留在永西、永南的时间较久,这方面做得较多。其要者有:
活捉王鸣岐。王鸣岐,名放风江,字鸣岐,永西酂城王竹园人。是永城第一号劣绅。1939年初,新四军来永后,打击和清除了日伪和杂八队力量。偏永西一隅的顽县长王化荣,五、六月离永他去,我方委任王的第一科科长徐风笑代理永城县长(不久既为县长)。可是,顽方又委任王鸣岐为顽永城县长。王被委任后,带着十多个县府官员,十几支长短枪,从亳州方向,秘密潜回永城的龙岗一带,准备聚集力量与我争夺永城的领导权。我抗日成果,岂容他人染指?
经批准,1939年六月的一个夜晚,杨斐率三中队由副中队长刘晓东带领的几个班(其中有谢俊卿任班长的一个班),直奔王鸣岐在白庙附近的驻地。把门剁开后,王等还在梦中便做了俘虏。我除缴获王部的全部人枪外,还缴了王鸣岐的大烟枪和县长大印,以及其他物品。王鸣岐的驳壳枪(为扒子钩)修配后由中队长使用。
不久,学生大队把王鸣岐一伙交永城县府,县以后又把他交永城独立团看押,四一年反顽斗争时,因环境恶化,过路前方把他处决。
智擒菊华生。菊华生是永南的一个惯匪。日军来后,他是杂八队的一个头目。他经常住他的姘头处。我掌握情况后,1939年六月的一天拂晓,学生队突然包围了菊的住处,由盛瑞堂出面请菊出来谈话。菊华生带一把双响的快慢机由随员陪同出来,他看势不好,便想拔枪抵抗,枪未取出,即被缴下(随员逃跑)。撤离该村的路上,把菊处决。快慢机(学生大队唯一的一把快慢机)由杨斐使用,后又转交寿松涛。
三中队还枪毙了土匪头子王秀云、孙XX(孙殿英的家族)、蒋XX;镇压了汉奸吴传鼎。永西人民称颂学生大队为“玉面包公”部队,有冤有仇均找学生大队去诉。
四、几次较大的变动
学生大队成立的四个多月中,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
首先,调整大队干部。1939年1月,大队长王振邦调永南地方大队(该大队辖徐文英一个连)任大队长,中国永城县委书记寿松涛兼任大队长;李品立调永城二区任区长,米蕴辉任政治指导员;盛瑞堂虽留任,但他是永城县委委员,分管一、二区党的工作,已很少随学生大队行动。
不久,杨斐调永城一区任区大队长。
随大队干部变动的还有:
刘嘉贞任学生大队副官;陈杰、吴淑坤调永城县妇联;贾铁梅(女,方中铎的爱人)任学生大队宣传队长。
撤销组建不久的大队特务中队(该中队四个班,五、六名党员),副中队长陈继增回一中队任中队长,指导员刘宝亮任一中队救亡室主任,部队并入一中队。寿去后,大队成立了卫生组,蒯汗杰任组长,蔡新?、蔡新安、蔡振铎等五人任组员。
寿松涛到任后,叫副官发给每人五角钱的永城流通券(一种粗糙的牛皮纸票子)。第一次拿到零用钱是很高兴的,虽然只有五角。
这时,游击主力集中开辟淮上,由学生大队留守永城,其活动范围扩大到全永,重点是永南。
其次,改变番号。1939年1月,部队活动到马桥一带发了夏装,并改永城学生大队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大队,成为支队直接领导的部队之一。
第一次穿上军装,带上新四军背章,一扫“土八路”的外表,显得颇神气。1939年七月独立大队去高庄一带活动时,群众无不投以钦羡的目光。当时一些人争着和学生大队拉点关系,请领导吃饭者络绎不绝,甚至排不上号。
大队人马驻李暗楼时,贾铁梅住李品立家。她穿着短裤,留着短发,开朗而且豁达,像一个活泼天真的小伙。她曾引起村中男女老幼的围观,成了李暗楼的第一号新闻人物。似乎她的一举一动都叫人好笑:院子里有棵枣树,枣还未红,她非要大娘打给她吃;她把辣椒叫“辣子”,一天三顿都叫大娘给她炒辣子;她把笔(bei,永城方言)叫笔(bi),说她的笔坏了要借李品立的笔用,大家更笑得捂不住嘴……她指挥宣传队唱《保卫马德里》等歌曲,劲头十足,大方而且带有洋味。总之,从她身上看不出知识分子和闺秀之气。李品立同志的母亲一提起贾铁梅,便乐得合不上口,老人家常向人打听她的消息。这大概是永东人民看到的第一位新型的革命妇女。
不久,宣传队被取消,贾铁梅回游支三团政治处工作(以后她又调去抗大四分校,任女生队指导员)。
从永东回永南后,独立大队便常和游支三团靠近驻防,三团政治处常派人去独立大队指导工作和筹办纪念“八一”活动。纪念“八一”大会是和三团一起开的。从形式上看,独立大队此时似已附属三团领导了。
第三,编入三团。1939年旧历八月十五日前,独立大队正式编入三团,成为三团三营。一、二、三中队,编为七、八、九连。干部作了调整:大队长、政委回永城工作,米蕴辉仍任政教;一中队(七连)连干未动,二中队(八连)连干回地方工作,陈体恕任连长,刘宝亮任政指;三中队(九连)暂留永城活动。改编后,支队政治部从学生出身的干部战士中,抽调一批人去支队政治部培训。被抽调的有:刘永岑(原学生三中队政指)、谢俊卿、尹传良(三中队排长)、邵士杰(三中队救亡室主任)……培训后任连指导员,大部去了西华部队(游支二总队)。
三团是游支三个主力团之一,当时只有两个营,急需充实。改编学生大队的同时,还把永南三区胡克明大队,编为四营。
扩充后的三团,部分团、营干部:
团长周时源,政委方中铎。
一营、营长张永远,营的代号“西湖”;二营、营长兰桥,营的代号“巢湖”;三营、营长姚元清,营的代号“洪湖”;四营、营长胡克明,营的代号“黑海”。
1940年年初,八连(原学生二中队)调为一营三连。姚元清营长,喜欢这个部队,曾为八连的调走,流了眼泪。
以后兰桥率三团二营返濉杞太,扩大了濉杞太独立团,三营,随改为二营。
学生大队编三团后,开赴亳东活动,在观音堂、刘集过的八月节。从此,活动地区,便不限于永城。“学生大队”这一名称,也仅存于永东屠庆太部。
五、综述
回首笑看往事,更感岁月峥嵘。回忆起学生大队,似使人又回到火热的抗日战争年代,产生对往事的无限怀想。
学生大队是我党、我军直接培养抚育下,和敌伪顽匪的斗争中成长的一支部队,年轻、纯洁、朝气蓬勃。它不仅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也有较高的文化;它土生土长,根深苗正,和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和永城人民有血肉的关连;它在永城有较大号召力,因而也具有较大发展前途。学生大队成立之初,就紧紧跟随党前进,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很快打消了乡土观念,抛弃个人利益,服从党的需要,愉快地编入主力部队。
学生大队,独立存在的时间虽然不久,然而,它却起到了它应起的历史作用。学生大队的成立,标志着永城第一次有了党领导的武装,打破了敌伪顽匪的一统天下。
同时,振奋了永城人民的抗日精神,推动了永城的救亡运动,配合游击支队,打击敌人,开创了永城抗日根据地,向军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干部。因而学生大队在永城人民中留下了较深的影响。永东一位老秀才赞颂学生大队的一首诗:“八路四军万众钦,幸儿参加学生军。同仇敌忾救中国,老夫耄矣亦笑频。”颇能代表人民对学生大队的感情。
1939年,正是游支大发展的时候,缺少干部,缺少知识力量。学生大队编入游支主力,正适应当时的急需,其中很多人被部队迅速培养为基层干部。从1939年初到1940年上半年,学生大队的学生队员,绝大多数当了干部。据我所知,任连指导员的就有:刘传新、刘宝亮、屠庆元、刘永岑、刘便钦、翟宝三、翟宝树、屠庆春、周法言、蔡铎、邵士杰、谢俊卿、周尚文、蔡新洁、尹传良、赵秀……这里还不包括相当于连指导员的一批机关干部和新永东学生大队的干部。
学生大队成立后,也正是永城开辟新区,建立基基层政权的时候,学生大队便向地方输送了一批干部。初建的永城二区干部,大部是学生大队的成员。如李品立、蔡新铭、赵子杰、蔡振纲、屠云乾、张化东、张彦秀……还有其他区的。
现在看来,把学生大队补充主力部队,固然是件好事。然而从长远和发展的观点看,这样好的一支部队,过早地编掉,不能不大大地限制它的发展可能和作用的充分发挥成了一个遗憾!如果采用主力“地方化”的形式,排个把主力连队到学生大队进行传帮带,学生大队就会被很快“孵化”出来,或再让它独立存在一个时期,派一些外来干部加强领导,然后由大队而团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一个团是毫不困难的),再加入主力部队的序列。其作用就不只是一个“补充营”了。这样看来“慢”点的方法,发展起来的部队,往往比较巩固。比那种整团编过来没经过很好改造的部队,要好得多。可以设想:学生大队如发展起来,绝不会走刘子仁的道路,相反,它还会作为一种抵制力量,在一旦出现了类似刘子仁事件时,使永城的局面不致那样急剧恶化。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责编:管理员)
Copyright © 2012 by yclsw.org. all rights reserved. 豫ICP备1400467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