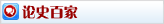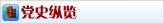永城明代“状元碑”考议
发布时间:2015-1-26 12:49:28 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7825
几年前,修济祁高速公路永城段时,曾在高庄镇曹河涯丁庄村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一通墓碑,惊动了我省媒体记者,做了新闻报道,说是发现了永城明代“状元碑”,墓主为湖广总督丁军善,其两个儿子皆考中状元。这通墓碑的出土非同小可,在永城历史上应是载入史册的大事,但是在明清《永城县志》上却从没有这样的记载,也压根找不到墓主的名字。笔者深感困惑,难道县志遗漏了吗?
主管永城文物工作的市博物馆馆长李俊山俊山看到报道,亦感到疑惑不解。李俊山从事永城文物考古工作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为资深专家和著名学者,对永城境内的历史和文物了如指掌,但对这个“状元碑”却是第一次听说。为一探究竟,彻底弄明白“状元碑”的情况,李俊山约我一块去高庄镇丁庄村查看。
其实丁庄村离东城区并不远,我和李馆长驱车过了东环路和汪楼沟,翻过古运河,越过济祁高速后就到了。在丁庄村村头遇见一位在地里干活的老人,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领着我们走进村东一户院落里,在一棵粗大的梧桐树下,斜放着两块方方正正的石碑,老人说这就是当年修路发现的古碑,老人招呼围观的村民将两碑的正面放平,擦去泥垢,又用清水洗刷一下,可以看出碑体很完整,碑文非常清晰,当看到碑文最后的落款时,李馆长对我说,这个明代石匠还是和你同姓的人呢。我一看果然有“盛养德”三个字,心里顿觉有一种亲近感,待水渍干后,李馆长从车上取出拓印工具,进行拓印,经过拓印后的碑文十分清楚。
碑铭盖是一行篆字:“皇明敕封丁光军元配张孺人墓志铭”,碑文兹录部分如下:“皇明诰封孺人张氏墓志铭。岁进士任湖广郧阳教授眷生张庆裕顿首拜撰,邑庠生子婿张承烈沐手书丹:余不侫素与京卫丁君善,京卫君元配张孺人终内寝,其子太学文学二君匍匐来请志,余谢不敏。文学君曰:‘里中推伯氏为彦,方思欲得一字,以为先孺人华衮,死且不朽。’余再谢不敏,太学君复曰:‘以家大人之莫逆伯氏也,且茑萝有松柏之附,因敢以先孺人之状,欲徼惠于下执事,死且不朽。’余闻之不觉敛容,义无固辞矣。乃请状,即读,已肃然,曰:‘是吾所当志也。’妇有四德而非,其至孺人有至德,超出四德之上,是余不侫所素习于耳者,是吾当所志也,谨按状。孺人为甬上郡丹城张公之女,张公于甬上为著姓,家殷殷后生孺人,不欲轻偶,为之相,攸得京卫君奇之,遂委禽马,及筓归京卫君家。人咸附耳语曰:富家女恐难以归顺也,庙见后,孺人即于早旦时,侯翁姑寝,门外问安。已又修髓,手羹汤进之,翁姑乃悦,更恂询然……以纺绩佐京卫穑事,且勤能俭,无重珥重锦,又奉无酺酪浆酒之费,一担米,一丝缕,靡不经画,而御下若疆以西旅单众,靡不帖,然养一家是以隆隆起,足轶陶朱也。京卫君,姓好施,始闾闬饥,饿殍相望,孺人为之赈粟煮粥,活者不下数百余。里人颂京卫君不休,悉京卫君之力也。京卫君将之白下任,以太孺人病不能行,孺人曰:‘吾亦能代为子也’。太孺人劝,延促京卫去。孺人奉甘脂,晨昏定省弗厌,亦弗倦。后太孺人又病,沉珂将就木,举家癫瞀计无生,孺人跪劝汤药,不解髦也,左右者四十余日,且每夜籁天顾以身代也。太孺人病稍革,泣曰:‘贤哉!妇何自苦若是?’孺人曰:‘代儿奉母,愧妇无以报,姑恩也。’语讫,太孺人瞑目,孺人痛几绝,不啜粥者五日,闻者以为大孝……京卫君泪摇摇不收,口噤噤不能语,绝缨者三,抚心者数痛母也,感孺人也,犹及记夫京卫君逾不休之年尚没举子,孺人疾首相向曰:‘是不可寒心也’。京卫君谢,不欲孺人。默逆之,为之置贤媵吴西二氏。吴生文学君鼎陛,西生太学君进艮,皆丈夫子。子当龆龀时,抚摩顾复者孺人,稍长,就外慱恤温饱起房者孺人,弱冠后,篝灯荧荧达丙夜,以幣光伴诵读者孺人。洎四子成立,均补博士弟子,秋毫皆孺人赐也……余不侫所谓孺人有至德,超出四德之上,是吾所当志者此耳。张子曰:孺人之事,舅姑也,有桓少君挽车之节,其相京卫君也,有乐羊断机之规,其教丈夫子也,有郑夫人以获画地之操,孺人贤乎哉!是宜为之铭。铭曰:……惟孺人徽行,以马孝以相,而天慈以宜而男志者,曰是闾门中之圣贤。崇祯甲戌冬一阳之月朔有一日。石匠:盛养德、吴玉纲、仝勤。”
从以上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方墓志铭,刻制的时间是在明朝末年,崇祯甲戌即1634年,距离明朝灭亡还有10年,那时明朝内忧外患,动乱迭起,危机四伏。该碑铭是为丁光军的元配张孺人而立的,孺人在古代原是对七品县令配偶的尊称,后来在明清演变为对妇女的通用尊称。在该碑文中,看不到湖广总督的官衔名称,也看不到“丁军善”这个名字,更看不到所谓的状元,可能是刚出土时,当时人们辨别不清或未读懂碑文,错读造成以讹传讹。这个所谓的“状元碑”其实是对张孺人的表彰和赞颂碑。张孺人是浙江宁波人,碑文中的“甬上”即现在的宁波。张孺人的丈夫丁光军在南京某部门做一般官员,碑文中白下即古代南京。张孺人作为南方大家闺秀下嫁永城,是否能够入乡随俗,起初是颇受质疑的。但张孺人不但生活勤俭,而且持家有道,更值得称赞的是,她非常仁孝、慈善。在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照顾婆婆,精心呵护,赢得乡邻称赞。在饿殍相望的饥荒之年,“赈粟煮粥”救活数百人,这应该是大仁大义。张孺人自己不能生育,为承续丁家香火,又主动为丈夫置媵二人,生育后代,自己像亲生母亲般照顾孩子,孜孜不倦,关心备至,直到把孩子养育长大,还伴其读书,使孩子皆考中秀才。
这样一位妇女,在忠孝悌义各个方面都赢得赞誉,在明代堪称楷模和典型,非常完美,所以撰写碑文的张庆裕称其为“圣贤”,就是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丁光军究竟任什么官职,在清代《永城县志》里查不到,不排除遗漏的可能,但此人不可能是科考出身,因为明清时代所有科班出身的秀才、贡生、举人、进士均可在县志里查到。撰写此碑文的张庆裕在清代《永城县志》里有记载,为明朝万历永城贡生,后仕至陕州学正。据丁庄村老人介绍,该村丁氏是明代兵部尚书丁启睿、户部侍郎丁魁楚的后裔,丁启睿、丁魁楚是永城马牧丁老家人,因当时家族显赫权贵,非常富裕,在永城东部购置田地数千亩,丁氏族人的一部分遂迁居于此,安家落户。墓志铭中的丁光军之所以去南京做官,据丁庄村老人世代相传跟丁启睿、丁魁楚有很大的关系。根据清光绪二十九年《永城县志》记载,丁启睿在崇祯己未年(1619年)任南京兵部主事,崇祯辛巳年(1641年)升任南京兵部尚书。丁魁楚曾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任保定巡抚,崇祯七年(1634年)任户部侍郎。丁氏家族在明末是永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丁光军很可能在南方任职时有缘结识宁波的大家闺秀张氏并喜结良缘,从而演绎出一段佳话。
该碑作为珍贵的历史实物,展现了明末永城历史的一角,彰显了永城民风的古朴和淳厚,张孺人尊老爱幼,相夫教子,救济穷人,乐善好施的精神和唐代永城著名的“孝友俊山”朱仁轨一样,都显示了永城自古以来秉承的仁孝精神和大孝大义,至今仍然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责编:管理员)
Copyright © 2012 by yclsw.org. all rights reserved. 豫ICP备14004675号-1